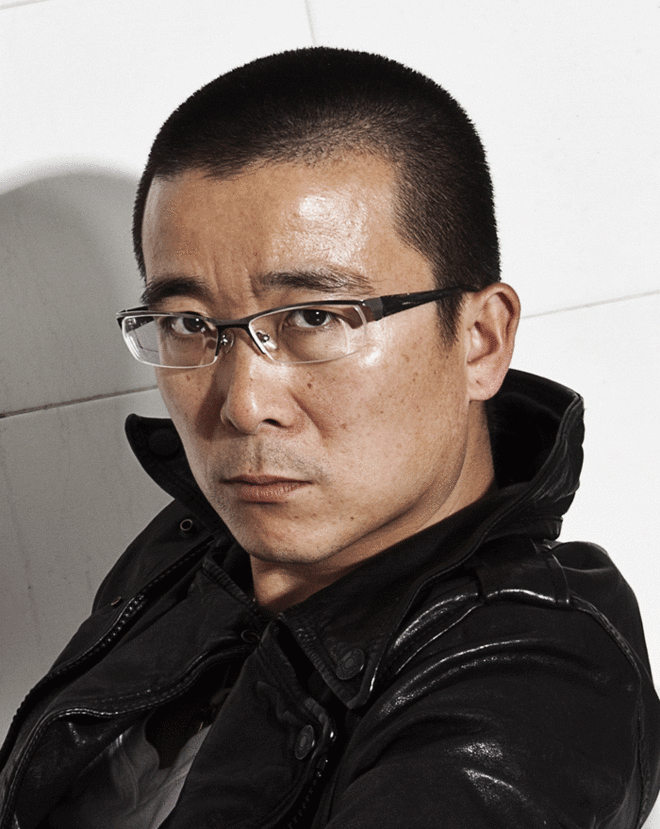|
赵亮:我要重新找到让自己的表达更舒服的方式时间:2015-07-30
在中国当代独立纪录片作者群体中,赵亮是经历极为复杂的一位,他既有着“学院派”的出身,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深造,又有着早年进驻圆明园艺术家村、做“北漂”的丰富经历,他的作品取材既包括生养于斯的乡土现实,也紧贴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生活,着力发掘时代命题下个体的生命体验。他的艺术创作不限于纪录片与个人电影,也在诸如录像、摄影等当代艺术实践中相互生发。在他的作品序列中,既有他最早作为“DV时代”与新纪录片运动中一员的可贵个体历史书写,有他拍摄十余载、获誉无数的《上访》,也有他与商业电影合作、记录幕后故事的《在一起》。而赵亮的难以被定位,更建基于他作品中的独特性,因此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如《罪与罚》、《上访》中,予人最深刻印象的除了题材本身的敏感性与指涉现实的复杂性,还在于他创作手法的沉潜有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更看重优雅的表达”。
《告别圆明园》《纸飞机》:一代人的怕和爱 1990年代初,赵亮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电视台,不久便因为工作需要赴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再加上其自身倾心于一种“浪漫”、“乌托邦”的生活图景,因此骑山地车从辽宁丹东一路驶往北京之后,再也罔顾家乡电视台的本职,开始加入“北漂”一族,成为众多怀揣艺术理想、涌向北京的寻梦大军中的一员。 在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片摄影专业学习的同时,赵亮混进当时艺术家群集、聚居的圆明园艺术家村,在赵亮的自述中,他最初选择了纪录片而非故事片,一方面在于技术上的易操作性与小型DV机器的便宜可得,另一方面因为其时他获悉了画家村即将被取缔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赵亮于1995年开始了《告别圆明园》的拍摄,赵亮将镜头对准他身边的画家朋友,记录了重要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个人遭际,与吴文光的《流浪北京》一起,《告别圆明园》勾勒出那个时代艺术家在寻找物质与精神家园之途中的内心惶惑,同时在赵亮的创作履历中,个人与体制、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第一次浮现出来。 1995年冬天将至,圆明园艺术家住户被警察强制驱散、迁出居所,赵亮的拍摄也告一段落。但这些素材随后被弃置,直到赵亮渐渐寻到串联组织的方式,才于2006年剪辑完成。在剪辑完成的《告别圆明园》中,赵亮的镜头捕捉到一种暗潮汹涌的城市生活状态与现实,连“持摄影机的人”在遭遇危险境况之时的现场也被完整保留下来:影片中有一处,赵亮在面对警察落荒而逃的同时,摄影机如影随形,镜头画面剧烈摇晃,而被问及携身所带是照相机还是望远镜,赵亮以一句“望远镜!”搪塞过去。 1990年代的民间影像之巍为大观,正是在于纪录片工作者们提供了在相同或者相近的社会议题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而在赵亮的下一部影片《纸飞机》(以拍摄素材顺序)中,影片拍摄的对象在当时更可谓众声喧哗,尤其是在第六代电影导演的早期创作中,摇滚青年代表了青年影像文化中最庞大、最富话题性的群体,赵亮的《纸飞机》刻画出一群年轻人在摇滚文化的浸染中吸毒、逃遁现实的生活状貌,影片充斥了影片主人公——一群朋克青年们无以慰藉、混乱流离的生活纪实,粗口、血管、针头、自杀……在面对社会转型之际价值观的虚妄与遽变时,他们选择了另类激进的方式,赵亮置身其中,镜头冷静而极富感染力,不同于《告别圆明园》中拍摄对象的激愤,《纸飞机》中的主人公情绪更为暧昧摇摆,同时不乏反省,影片结尾,躺在床榻上垂死的青年说:“这部片子就叫《纸飞机的故事》吧。它想飞,但是还是飞不起来的,因为它是纸做的。”
《在江边》《罪与罚》:边境上的“关系学” 2004年,赵亮回到家乡丹东,着意于考察中朝边境的社会生态,《在江边》与《罪与罚》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诞生的两部纪录作品。在《在江边》中,赵亮访问了居住在边境附近大量的中国本地住民、朝鲜生意人,同时与几名边境守卫“相遇”,在这部作品中,赵亮表现出更为娴熟的结构叙事能力,将一系列不为因果的事件点滴组织成篇,纷呈的现实关系在作者的亲历中渐次展开:朝鲜街头的“红色”景观、边境的法则与灰色地带、公开贸易与地下黑市共存、普通百姓充满超现实色彩的生活“原生态”,等等。 而《罪与罚》则集中聚焦在一边境派出所的日常事务工作上,包括出警、民警与犯罪嫌疑人周旋等,几桩案例中的主人公清晰可辨:一个被查出营业许可证过期的拾荒老汉面对警察经受着尊严的考验、有听觉障碍沟通困难的盗窃嫌疑人拒不承认偷窃、偷伐林木的农民在连夜刑讯下道出为生活所迫的原委,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三名伐木农民被审的内容,又成为赵亮一部三屏录像装置作品《中国忏悔室》的主体。在这些被审人之外,赵亮还饶有兴致地把镜头对向了民警们,一名老兵在退役临行的前夜苦饮,放声发泄内心的困窘与无奈。赵亮尤其强调民警这一群体在作为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之外,与一般人无异的个体性,因此审讯打人,双方在人与社会的某种关系中都处于受害者地位,并且共同构成了荒诞的生存现实全景。 《在江边》与《罪与罚》对赵亮而言,在艺术上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一方面赵亮对组织素材更有心得,同时也有效地建立起个人化的隐喻方式,比如在《罪与罚》中的不同审讯间隙,赵亮多次展现了两条狗的场景,一只狗最终被一名警察宰杀,赵亮用这一具有连缀性的场景作为隐喻,他说:“暗示和勾画了受害者和对普通人行使权力的警察之间的关系”。
《上访》:中国问题与公共意识 1996年,赵亮在北京南站的一个聚居点偶然遇到了上百号的上访者,状如乞丐,衣衫褴褛,四处是临时搭建的棚屋与用来做饭的锡桶,而在北京南部的永定门附近,紧邻北京南站,正是国务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的所在地。这一区域成为上访者的聚集点,作为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在长年上访而未获结果的历程中益发窘迫,但从不轻言放弃,坚韧如一,在这个无限循环的荒谬体系中,赵亮同样生出深入其中的韧性,跟踪一对母女历时十二年之久。在长达318分钟的完整版中,影片采用了三部曲结构,由《上访村》、《母女》和《北京南站》三部分组成。 《上访》的第一部分围绕上访人群的生活处境与各异的上访方式展开,而在最具华彩的第二部分《母女》中,这一对母女来自江苏泰州,母亲戚华英从1987年以来就在不断上访,4岁的女儿方小娟紧随在旁,她的父亲在一次医院的常规检查中被要求输营养液,过程中猝然死亡,尸体在戚华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仓促强行火化,戚华英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诉,无果而终。从此,戚华英坚持上访,走上漫漫路。在赵亮的影像记录下,方小娟失学十年,长大成人。因为对身世的知悉(非戚华英夫妇亲生),方小娟最终选择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北京。此后,方小娟回乡,被信访局长张某认作干女儿,张某的“抚养”事迹被媒体大肆报道,小娟的父母却被变相判定为“脑溢血”与“偏执狂”。母女暌隔日久,直到小娟结婚诞下一子后,重回北京寻找母亲。戚华英因失实报道耿耿于怀,最终服膺于亲情的呼唤,母女终于相认。生活本身的戏剧性教人喟叹不已。 在《上访》的第三部分中,为筹办北京奥运会,南站开始改建,南站附近的所有建筑,包括上访村均被夷为平地。上访者们失去“应许之地”,陆续离开。同时本地居民因出租房屋受到牵连,从而也加入上访大军,吁求自身利益被重视。影片中,赵亮拍摄了拆迁的过程及上访村的一位业主,他对强拆进行抗议,在房屋被拆毁后留下的垃圾场下搭建窝棚,拒不搬离,风雨不改。 “上访”已经成为中国问题,其势之广、其参与人数之众,俨然是社会公共空间中不可规避的重要议题,但直到赵亮的《上访》,我们才窥得其中之社会实相,赵亮在创作这部影片时不乏介入公共话语、甚至推进社会改革的野心,而影片最后呈现出庞大的社会性架构,以及描摹个人命运的强烈张力,成为当代影像记录中最丰饶的收获之一。
《在一起》:并非转型 《在一起》是赵亮接手的一项命题作业,对于故事片《最爱》筹拍伊始顾长卫的邀请,赵亮抱着一颗学习的心,进入了《最爱》剧组,投入拍摄剧组中几位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同时,赵亮还是尝试了在命题之外,个人对题材一定深度上的开掘,因此在《在一起》中,另一部分内容是赵亮通过QQ群寻访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患者,征集选定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剧组参与拍摄。 作为《最爱》的姊妹片,或者说套拍纪录片,《在一起》获得了难得的放映机会,这也是年届40的赵亮,第一次将纪录片送进电影院、在国内公映,而在选择之初,面临可能在命题约束中无章可做的问题,赵亮强调“勿以善小而不为”,“让感染者的生活能有一点点的改善就很好”,同时并不讳言这部影片与前期独立创作之间的不同,称《在一起》是一个特殊案例。 在影片的拍摄中,赵亮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恐惧消除的过程,并在直面艾滋病患者的艰辛和苦楚时,时而伴有焦灼的无力感,这在《在一起》的成片中却付之阙如,影片中剧组人员与艾滋病患者自然相处,无论是少年胡泽涛,还是老夏,都感受到了剧组人员的温暖,影片结尾,一名征求拥抱的艾滋病患者吸引了路人的纷纷关注,有人热情投怀,有人表情生疑,或许,对于艾滋病患者在社会人群面前的被接受程度与社会关怀度,这才是赵亮隐而不发、投诸更多思考的节点。
“我对以前的拍摄方式比较厌倦了” 从电影的角度来讲,你的纪录片的师承是什么样的? 我其实没有太具体的师承,这么多年的磨合,像我也做影像艺术啊,拍照片,我对影像也有自己审美的一些角度和方法,当然国外的那些电影大师对我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么多年走过来是一个综合的磨合的过程,具体说哪一个人是我的师傅,没有。我没有受某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大,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没有看过几部纪录片,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冲动。 你现在是在忙什么片子呢? 现在没有具体的,因为我对以前的那种拍摄方式也比较厌倦了,都是特被动的那种状况,我想以后的片子是更接近影像艺术,更自由的表达我自己。我得自己找一个喘气的机会,反思一下自己作品的方向吧。所谓被动,就是以前拍纪录片你老盯着这一个故事,天天要跟着,这样对创作本身有时候是一种驯服,经过这么多年我也厌倦了,总是在看别人的生活,我自己都没有生活了,空的一样。我觉得我要重新找到让自己的表达更舒服的方式。 那你可以去拍故事片,那就真的是完全创造了。 都可以,没有非得强逼着自己去拍一个纪录片,也不一定非得拍片子,有一天兴许我写诗呢(笑)。艺术最重要的是创造力,我刚才所谓的被动就是,你如果按照套路去想问题、叙述的话,就陷入纪录片的这样一个圈套了,陷入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里边就很难再出来,一旦要出来,你的故事稍微不一样,就有人因为你之前的模式觉得你不对了,现在我可能会让自己表达的更自由一些。 但是如果表达的更自由了,失去了以前的纪录片方式,你可能会得不到现在这样的认同? 没关系,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的表达,我能表达舒服才是最好,我也不想非搞得跟英雄似的,没必要那样,我从来也没想过那样。 我是那种很浪漫,很随性,很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但现在老弄得我跟英雄似的。 你是一直这样不需要得到别人认同吗?我想任何一个人,你开始时还是要得到别人认同的。 我也没说一开始就没有名利心,《纸飞机》入选马赛,我就高兴的不行了,一个月我可能什么都不干,就等着签证拿下来,我就去玩去了,得奖了之后又会马上告诉朋友,想让人分享自己的那点小欲望。现在得奖了,好吧,得奖了就往家里一放,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个阶段已经过了。 过了那一阶段,你会觉得这个都是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你真正需要的不是别人的认同。一个片子出来,别人会有各种看法,但其实你最终解决的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一定是问自己:你喜不喜欢这个作品,你究竟要做什么?我要真的是革命家的话,那我就拉杆子建党去,我去国外搞点什么,但没必要。我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来表达自己。 “《在一起》我觉得是挺牛逼的一个片子,对社会的影响比《上访》大多了。” 《在一起》之后有很多艾滋病人给你写信? 对,他们自己也很感动,看完都会哭,他们觉得社会应该多一些这样的东西,真正能促进和改善一些现状。他们认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他们觉得这个事情这么做靠谱,能有点意义,像12.1(艾滋病日)晚会,弄一些明星,拥抱一下,有真的作用吗? 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做的结尾挺灰暗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现实,整体对艾滋病还是一个悲观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想用这样的悲观去警醒世人。可是顾老师(顾长卫),从他的层面出发,说如果是有一个亮色一点的结尾呢,会让你有希望,这种希望会更多的促进人们的爱心,如果你真那么悲观,人家可能觉得算了,反正谁也拯救不了。所以什么是知识分子,不是书读多少,知识分子一定是引领人类向上的一个动力,这个精神是一定要有的,因为人类存在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需要一种引领,一种精神去鼓舞人们,把人类带往一个好的方向吧。 《纽约时报》之所以那么惹怒你,说明你还是很在乎外界怎么评价你的? 因为它的价值观扭曲了我的思想,所以我是反感的,我也不可能让《纽约时报》给我道歉,所以我就尽量少的去介入这些事情,因为一旦你要介入,一接受采访,完了可能一说话,不知道又是怎么写出来呢,《纽约时报》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就是借你的素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跟你自己没有关系。关键是他把我写成一个变节的人,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它非得这样给我泼狗屎,这个我受不了。是侮辱了我。 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一起》我觉得是挺牛逼的一个片子,对社会的影响比《上访》大多了,你看艾滋病人都给我写多少那种影片观后感,只要看了电影,确实是能改善人的一些既有看法,这是很好的,《上访》再大响动,别人看不到也等于不存在,没有产生意义。 你以后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开始拍的片子都是很强硬的,从某种程度上是站在这个现行体制对面的,你刚才说,你以后要做更自由的东西,或者更抽象的更艺术一点的东西。那可能就跟现实的关联没那么深,照样别人还是会说你软化了,对吧? 这个倒是没关系,仁者见仁嘛。艺术的品质不会差,对我来说就很好了,你看不到,你不懂,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不需要每个人都能看懂我的作品,我不需要对每个观众都讨好,我不需要非得迎合你们的一个观点,我有自己的活法,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我们对生命的看待对人生的看待可能不一样,为什么要强求我,前面都是我青春期的作品,后面可能是赵亮真正想做的东西,前面那是一个机缘一个契机,历史推到这儿了,我也恰巧拍了那些,如果下一个我还拍“上访”的话,对我来说是在浪费时间,可能很多年轻人他们还在拍,很多人都可以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不需要拍了。 “现在我可能更看重一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宗教是怎么回事,更愿意考虑广泛的事情。” 你觉得《上访》是那个时候没人关注这方面,所以说你才去做了这样一个片子? 那个时候兴趣也在这儿,觉得这个事很重要,确实有兴趣用历史的观点或者眼光去看,所以我去做《上访》。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可以去拍它,我可能就更需要别的感受,我可能会用别的方式去表达。 这个社会实际上越来越糟了,它没有刺激你有更多想去做什么的愿望?反而是你现在想离开你既定的方式? 我如果按照别人的想法,那赵亮的下一部作品应该是更尖锐的,但我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这样一个思维去把我套进去呢?没必要吧。 站在你现在的领悟力或者标准,看之前的作品,《上访》也好,《罪与罚》也好,你怎么评价它? 那都是过去式了,都是一些毕业作业吧,刚刚毕业。我没觉得是多好的东西,就是那么些东西吧,就是我那些年做了那些事,对我来说,从表达自己对艺术认识的方向,觉得那些东西还不足以让我很自信,让我很满意。 那时候的心智我只能达到那个水准,但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表达的更多,我觉得体制那些事我根本就不在乎,现在我可能更看重一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宗教是怎么回事,我可能更愿意考虑更广泛的事情。因为体制,在历史的长河里它就一瞬间。 所以你不希望自己表面看起来是个英雄,实际上是祭品,被祭上去的一个东西? 对啊,有这种嫌疑,赵亮去拍别的就不行了,我有很多摄影的展览,做装置艺术的展览,我可能换一个方式,用指桑骂槐的方式。 当作品不是出于本源的某种欲望或者说某种冲动去创作,它虽然说很聪明、很高级,会不会生命力往往反而不如之前的作品? 不会的,我觉得成熟的作品,按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青春期的生物本能的东西,和经过理性思考过得东西,还是差不少的,我觉得会更有力,因为那是经过了历练,经验,各种总结之后的创作,它可能更高级,可能不会生理性的去催人眼泪,可能理性的思考更多。(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