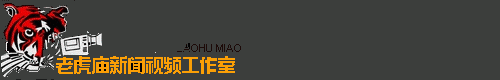|
拍《在历史这边》故地重游时间:2015-03-24 从九月五日旁晚开始,到十六日下午,我一直跟随着老虎庙(我习惯上更倾向于称呼他为张大哥)所拍摄的《在历史这边》摄制组,深入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大巴山里。对我来说,这是生命的一次旅行,也许还可以称得上是“尝试”,因为自己又收获了很多令未来受用无穷的新东西。而张大哥,以及剧组成员和跟随者们也许不是简单的这么想…… 长达十二天的时间里,我们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安康紫阳的芭蕉口,前后共八天。之所以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张大哥和他的伙伴们曾经在这里呆了两年多时间,襄渝线铁路其中的两个山洞就是他们修的。那时候,修铁路打山洞几乎全靠人力劳作,当时他们才十六七岁。青春,就像是定格的相片,或者回忆的影像,永远的遗留在那里。时隔四十二年,有些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些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当张大哥扛起机器的那一瞬间……
我想,我是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感受,苦难毕竟不是观察和领悟就能体会得到的。也许,透过收藏的点点滴滴,作为旁观者的角度,能够产生一些理解,自己就算是很幸运了。 我的幸运在于,不必被那个时代摆布命运,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追求;我的幸运是不必过分的为衣食和生存担忧,更无须在严重饥饿的状态下翻山越岭去扛木头抡铁锤做苦力;我更幸运的,就是能和张大哥一起,找寻那个年代的那些人…… 张大哥决心拍摄《在历史这边》纪录片一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我这样猜测是因为在正式的开机宴之前,他已经记录了八十多小时的影像资讯,所积累的材料和信息很充足……当资金、设备和人员等等全部就绪,就是故事正式开始讲述的时候。 《在历史这边》是讲述三线学员的故事。关于三线学员这样的称呼,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在一九七零年,他们是一群还在上初中的孩子,响应号召(按照他们当时的话说,就是“让毛主席睡好安稳觉!”)去支援襄渝铁路线的建设工作,代号7201工程。所有的三线学员,都是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学生,共有25800多人,年龄最小的据说还不到十四岁……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正式的称谓(按照政府官员的话说,你们既不是部队军人,不是铁道兵,也不是民工,只是一群学生),他们就好像是被遗忘的一群人,他们的那段历史如同并不存在一样。 实际上,那些三线学生所经历的困苦和磨难,也许是他们这一生中最沉重的经历,其中至少有48位青春花季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现在活着的人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二,而且大部分人生活困苦,无所依靠(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艰苦的劳动,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极大的伤害。有人精神失常,有人从此落下终身伤痛,甚至是残疾病躯。就算是顽强的人,也因为这两年工龄的“不存在”,在以资历划线来界定的生活工作中分房子、讲待遇、评职称等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影响)…… 四十二年过去了,活着的三线学员已经成为了“老人”,如果没有人去记录讲述那些历史,恐怕就会被带进坟墓,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开释的秘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段历史中,关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关注我们自己。 所幸,很多人在努力。通过那些挣扎的抗争,最近传出了对三线学员们的补偿消息,每个人每月两百元,对死去的生命一次性给予五千元……我真不觉得这是什么好消息:两百元在物价奇高的今天能做些什么?一条人命就值五千块? 文字不足以表达我的愤怒,所以我尽量让它显得平静一些。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艰辛,差别在于是否有一个公平的回报。同时,那些努力付出能否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我曾经对五六十年代的人有过一些偏激的看法,以为他们所有的苦难都是“咎由自取”,理由是他们的那个时代对我们的传统和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令到传承出现断层,几乎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可是,当有人问我:“刀口就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你要命,还是要理性?”我无言以对。 求生,是生命的本能,没有到那个时候,所说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道貌岸然的自以为是;做到的时候再说,生命才具有最真实的尊严。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那还只是无关乎生死时的抉择…… 人,是在适应环境下生存的。当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走在阳光大道上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去藐视那些曾经在阴霾泥泞里流着血汗的长者?也许,还有一个让我们的后辈们不再误解我们的可能,那就是铭记先辈长者的历史,让他们的背影出现在阳光下。 因此,从现在开始,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事情做起,爬山涉水寻找那些真实的历史,走街串巷探访亲身经历者的生活……聆听他们的讲述,站在真相这边,让自己不再迷茫。】 此次跟随张大哥拍摄《在历史这边》剧组进山,不但收获颇丰,还有惊喜。譬如张大哥告诉我照相技巧的关键:横平竖直(别看我玩了一年多单反,架势看起来像个摄影者,实际上连门道都不懂呢)!譬如从专业摄影师小刘那里学来找主题,表达简洁流畅的画面(这个有深度,我暂时掌握不了,因为小刘说我得“先看看理论”)……咦!说着说着就“露宝”了! 为了话题不至于过分的沉闷,我还要再透露一下剧组的概况。此次行程,张大哥说原本是想呈现“荒野求生”的画面,同时积累一些秋季景致的素材。剧组除了张大哥,还有杜春光和刻薄主人都是当年参与襄渝铁路建设的“学娃子”,另外《南都周刊》的文字记者阿涛和摄影记者小刘全程跟随…… 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不是说的太多啦?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