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电影导演 于广义时间:2015-03-24 于广义,1961生于黑龙江,现生活在大庆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多年来一直进行版画创作,2004年开始独立制作纪录片。 “我的开机仪式既简单又庄重,我一个人,跪在父母坟前,对他们说,我不画画了,要开始拍电影了。”
“身在一楼,却想着楼顶的事情” 东方早报:这次在国内获奖和在国外有何不同? 于广义:我拍了这么多年,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我。从原来到现在,我给自己定位很低,我就是个老百姓,然后拍老百姓的故事。我长在黑龙江的小林场,18岁前都没看见过火车,现在家乡变成雪乡了,成旅游区了。大风雪居然还能变成资源?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风雪给人带来的不便太多了,一场雪下个三天三夜,门都推不开。人闲的没事儿就围着火炉讲故事,谁家故事讲得好,谁家就显得有人气。我父母都会讲故事,我是听着故事长大的。我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拿着一份参考消息,他就坐在炉子边上给我讲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我知道我将来肯定会走出去,离开山沟,去很远的地方,做一件和我这些伙伴不一样的事! 东方早报:学画画是为了从大山里走出去? 于广义:对,走出去,我始终是一个,用很多人的话说,是不现实的一个人,总是在空中游荡的人,身在一楼,却想着楼顶的事情。后来终于有一天可以离开大山进入城里了,那是1978年的12月,我当兵去了,结果这趟列车给我拉到了内蒙古,中蒙边境的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山沟,我在那边干了三年,打山洞、挖战壕、救山火、收庄稼、建营房,虽然我没有下过乡,但我觉得这种经历就像一个老知青的经历。 东方早报:画画“说”不清楚吗?你一定要用电影、纪录片这种方式? 于广义:2004年,我家里来了个同学,他告诉我,今年是百年伐木最后一年,国家马上要天然林保护了,我们那个林区是从1895年开采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太重要了!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影响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持续久了,它就会形成一种习俗,这习俗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但载体没有了,一切就都结束了。黑龙江闭塞,保留了很多好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挖掘?当时就很有冲动,于是到了中关村买了套设备,店员告诉我开机关机,我就开拍了。很多人问我学电影的经历,我说就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觉得其实我不用去学什么,因为我会画画,我又会讲故事,我读了很多小说,把这些东西合到一起就是个电影。我带着机器,和伐木工人住了一个冬天。这些人都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 “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都省了吧” 东方早报:他们会问你,“于广义,你拍我们干嘛?”你怎么回答? 于广义:对,他们问过,我说我就是想记录你们真实的生活,他们说,“原来生活比这还艰苦,故事比这还多,你不来拍。”我知道它很重要的时候已经晚了。和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他们就习惯了。我拍了100多盘素材带,回来不知道怎么弄,在这之前,我都没看过纪录片电影,只知道有个罗伯特·弗拉哈迪。我进到大山里,憋了半辈子的话,能够通过电影说出来,一下子就好像找到出路了。第一个片子《木帮》剪了一年多,最后在很多电影节上都获了奖。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些奖认可了你什么? 于广义:诚恳,朴实吧。首尔电影节当时给了我一个评语,“一个未曾学过电影,甚至很少看电影的人,他用他的视觉带给我们一个未知世界”。因为我是在两种文明之间跳来跳去的人。我每年都会给我的父母上坟去,我的开机仪式,既简单又庄重,就我一个人,趟着过膝的积雪,12月的中旬,跪在父母坟前,说:“爸妈,我回来了!我不画画了,要开始拍电影了,我要拍一部我们山里人生活的电影。” 东方早报:你的片子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子,既有粗糙感又有情感中细腻的东西。 于广义:我酷爱俄罗斯文学。首尔电影节之后,很多人都在问,这些“木帮”下岗以后都在干什么。带着这个问题,2006年的冬天我又回去了,于是就有了《小李子》。《小李子》也是林场的下岗职工,这个故事里有猎人、女人、两只狗、一只猫。你想象一下,在北方零下30多摄氏度,两个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就像俄罗斯文学里的那种描写,带着淡淡的忧伤,在极为严酷的状态下,寒冷使人变得纯粹。拍纪录片这活儿很辛苦,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物质回报,所以你拍的时候,一定要说你憋了半辈子想要说的话,包括上一辈人的话,你都要替他们表达出来,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都省了吧,尤其是独立制片,我自己出钱我自己说了算。 东方早报:对于你熟悉的老乡,镜头里你的底线是什么? 于广义:我和他们是同类,如果没有我爹妈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也就是木帮,就是小李子,我可能还不如三梁子(《光棍》主人公)。至于那个底线,我想,是卑微而不下贱,他们活得有尊严。(早报记者 黄小河采访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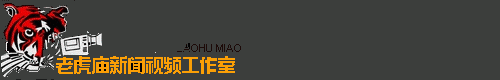
 43岁的时候,从山里走出去的于广义义无反顾地放弃版画事业,回到深山老林,去做一些与时间斗法的事情,制作具有社会人类学价值的纪录影片。这个半路出家、只花了一个下午学习“拍电影”的纪录片导演,只拍同一个地方——他的家乡,却以《木帮》、《小李子》、《
43岁的时候,从山里走出去的于广义义无反顾地放弃版画事业,回到深山老林,去做一些与时间斗法的事情,制作具有社会人类学价值的纪录影片。这个半路出家、只花了一个下午学习“拍电影”的纪录片导演,只拍同一个地方——他的家乡,却以《木帮》、《小李子》、《 很多人离开的时候说,将来尿尿都不冲着这个方向,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离开以后,我今年已经50岁了,其实我最怀念的就是这段日子,从林区那些伐木工人所讲述的神叨叨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故事,到内蒙古体验更加粗糙的生活,包括那种气候,这是我所受的最好的教育,加上父母省吃俭用送我去大学学画画,这就是我全部的知识来源。所以,无论画画,还是拍电影,它只能是一种语言,一个人无论他是做文字、画画,还是电影,他一定是有话想说,而且是那种非常强烈的。
很多人离开的时候说,将来尿尿都不冲着这个方向,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离开以后,我今年已经50岁了,其实我最怀念的就是这段日子,从林区那些伐木工人所讲述的神叨叨的伪满洲国时期的故事,到内蒙古体验更加粗糙的生活,包括那种气候,这是我所受的最好的教育,加上父母省吃俭用送我去大学学画画,这就是我全部的知识来源。所以,无论画画,还是拍电影,它只能是一种语言,一个人无论他是做文字、画画,还是电影,他一定是有话想说,而且是那种非常强烈的。



